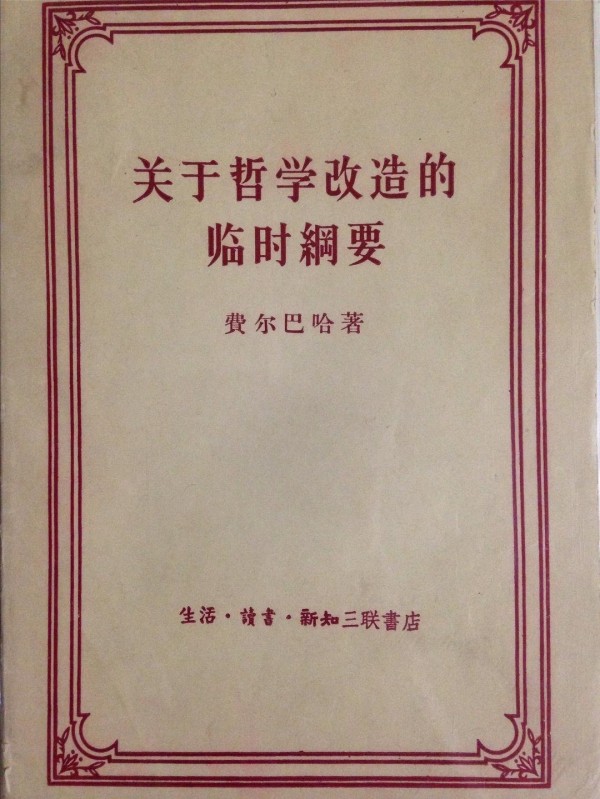2024-1-27 11:31 /
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思辨神学与普通神学的不同之点,就在于它将普通神学由于畏惧和无知而远远放在彼岸世界的神圣实体移植到此岸世界中来,就是说:将它现实化了,确定了,实在化了。
斯宾诺莎是近代思辨哲学的真正创始者,谢林是它的复活者,黑格尔是它的完成者。
“泛神论”是神学(或有神论)——彻底的神学的必然结论。“无神论”是“泛神论”、彻底的“泛神论”的必然结论。
基督教是多神教与一神教的矛盾。
泛神论是带着多神教的宾词的一神教,就是说:泛神论将多神教的那些独立的实体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的宾词和属性。例如斯宾诺莎便将作为思维的总体的思维,以及作为广袤物的总体的物质,当作实体亦即上帝的属性。上帝是一个思维的事物,上帝是一个广袤的事物。同一哲学与斯宾诺莎哲学的不同点,仅仅在于它将实体的死的、呆板的东西用唯心论的精神鼓动起来。特别是黑格尔将自我活动、自我判别力、自我意识当作实体的属性。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矛盾的命题:“关于上帝的意识就是上帝的自我意识”,与斯宾诺莎所提出的那个矛盾的命题:“广袤或物质是实体的一种属性”,是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面。这样的命题并无其他意义,仅仅是说:自我意识是实体或上帝的一种属性,上帝就是自我。有神论者归之上帝的那种与实际意识不同的意识,仅仅是一种没有实在性的观念。但是斯宾诺莎说:物质是实体的属性。这个命题的意义无非是说:物质是具有实体性的神圣实体。同一地,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命题的意义也无非是说:意识是神圣实体。
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经应用过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
泛神论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对于神学的否定。
正如按照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二和命题十),实体的属性或宾词乃实体自身,按照黑格尔,绝对的宾词、主体的宾词一般说来是主体自身。在黑格尔看来,绝对是存在、实体、概念(精神、自我意识)。但是,仅仅被思想成存在的绝对,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是存在。绝对如果被放在这种或那种规定、范畴里面思想,就完全融化为这种范畴、这种规定。因而除此以外,绝对仅仅是一个名称。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主体的绝对仍然是基础,仍然有着真实的主体,有着那种东西,由于这种东西,绝对才不是一个单纯的名称,而是某种东西:这种规定仍然经常具有一种单纯宾词的意义,正如斯宾诺莎的属性那样。
思辨哲学的绝对或无限,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只不过是不加规定的、不确定的东西——抽去一切规定的抽象,被看成一种与这种抽象不同而同时又与这种抽象等同起来的实体:从历史观点看来,则只不过是陈旧的、神学——形而上学的、并非有限的、并非人性的、并非物质的、并非确定的、并非创造出来的实体或虚构——,被看成行动的先于世界的虚无。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神学的神圣实体是一切实在性、亦即一切规定性、一切有限性的理想总体或抽象总体,逻辑学也是如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可以在神学的天国里再现,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也可以在神圣的逻辑学的天国里再现:例如质,量,度量,本质,化学作用,机械精造,有机体。在神学中,我们对于一切事物都是作二次考察,一次是抽象的,另一次是具体的。在黑格尔哲学中,对一切事物也是作二次考察:先作为逻辑学的对象,然后又作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对象。
神学的本质是超越的、被排除于人之外的人本质。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超越的思维,是被看成在人以外的人的思维。
正如神学先将人分割为二加以抛弃,以便后来再将这抛弃了的本质与自己等同起来,黑格尔也是先将自然与人的简单的、与自己等同的本质化为多数,加以分割,以便后来把那粗暴地分开的本质在粗暴地调和起来。
形而上学或逻辑学只有在不脱离所谓主观精神的时候,才是一种真实的、内在的科学。形而上学是秘传的心理学。只从性质本身考察性质,只从感觉本身考察感觉,将它们分裂成为两种特殊科学,好像性质是脱离感觉的东西,感觉是脱离性质的东西,这是多么任意,多么粗暴。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与自己分离了的所谓有限精神,正如神学的无限本质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有限本质一样。
按照黑格尔,绝对精神是显现或实现在艺术、宗教、哲学中。用直率的话来说:艺术、宗教、哲学的精神就是绝对精神。但是不能把艺术和宗教与人的感觉、幻想和直观分离开来,不能把哲学与思维分离开来,简言之,不能把绝对精神与主观精神或人的本质分离开来,而不重返旧的神学观点,而不将绝对精神当作另一种与人的本质有别的精神,亦即当作一种在我们以外存在着的幽灵而使自己迷惑。
“绝对精神”是在黑格尔哲学中还作为幽灵出现的神学的“死亡了的精神”。
神学是对于幽灵的信仰。不过普通神学有它的感性想象中的幽灵,思辨神学有它的非感性抽象中的幽灵。
抽象就是假定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本质。黑格尔哲学使人与自己异化,从而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的整个体系。它诚然将它分离开的东西重新等同起来,但用的只是一种本身又可分离的间接方式。黑格尔哲学缺少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理。
从人抽出来而被抛弃了的人的本质与人的直接、鲜明、毫不暖昧的等同,是不能用正面的方式从黑格尔哲学中引出来的,只有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才能从其中引申出来。我们只有将这种等同理解成思辨哲学的全盘否定,然后才能理解、才能了解它是不是思辨哲学的真理。虽然一切事物都包藏在黑格尔哲学之中,但是这些事物经常都带着它的否定,它的对立物。
艺术一目了然地证明:绝对精神就是所谓有限的主观精神,因为绝对精神与这种主观精神是不能而且也不该分开的。产生艺术的,是那种以此岸生活为真实生活、以有限者为无限者的感情,是那种以一定的实际本质为最高的神圣本质的热情。基督教的一神教并不包含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原则。只有多神教,只有所谓偶像崇拜,才是艺术和科学的源泉。希腊人只是无条件地、毫不犹豫地将人的形象当作最高的形象,当作神的形象,因而才能达到使他们的造形艺术完美。基督教徒只有实际上否定了基督教神学,将女性的本质当作神圣的本质加以崇拜时,才走向诗歌,当基督教徒对宗教的本质进行想象时,当宗教的本质成为他们的意识对象时,他们就与他们的宗教的本质发生了矛盾,成为艺术家和诗人。彼得拉克由于宗教才悔恨他神圣化他的劳拉的那首诗,何以基督徒不能像异教徒那样具有与他们的宗教观念相适应的艺术作品呢?何以他们没有完全满意的基督形象呢?因为基督徒的宗教艺术由于他们的意识与真理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二失败了。基督教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的本质,而在基督徒的意识中却是一种另外的非人性的本质。基督应该是人,同时又不是人:他是一种暧昧的东西。但是,艺术只能表达真实的东西,不暧昧的东西。
人性的东西就是神圣的东西,有限的东西就是无限的东西;这个果断的、变成有血有肉的意识,乃是一种新的诗歌和艺术的源泉,这种新的诗歌和艺术在雄壮方面、深刻方面、热情方面都要超过以前的一切诗歌和艺术。对于彼岸事物的信仰,是一种绝对没有诗意的信仰。痛苦是诗歌的源泉。只有将一件有限事物的损失看成一种无限的损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热情的力量。只有回忆不复存在的事物时的惨痛激动,才是人类的第一个艺术家和第一个理想家。但对于彼岸事物的信仰,却将各种痛苦变成幻像,变成虚构。
从无限的东西引申出有限的东西、从不确定的东西引申出确定的东西的哲学,是永远不能达到对有限的东西和确定的东西作出一个真正的肯定的。从无限的东西中引申出有限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把无限的和不确定的东西确定了,否定了。必须承认没有规定、亦即没有有限性的无限者,只不过是无限者的实在性,因而假定了有限者。但是虚构绝对的否定性仍然是基础,因此被假定的有限性经常又被扬弃了。有限者是无限者的否定,同时无限者又是有限者的否定。关于绝对的哲学乃是一种矛盾。
正如在神学中,人是上帝的真理、实在性——因为一切将作为上帝的上帝现实化、将上帝化为实际本质的宾词,如力量、智慧、善、爱、甚至无限性和人格,都是以异于有限的东西为条件,所以首先要假定在人之中,与人在一起——,同样的,在思辨哲学中,无限的真理也是有限者。
有限事物的真理性,绝对哲学是用间接地、颠倒的方式来宣布的,如果只有当无限者受到规定,亦即不把它假定为无限者,而把它假定为有限者的时候,无限者才存在,才有真理性和实在性,而那么,实际上有限者就是无限者。
真正的哲学的任务,不是将无限者认作有限者,而是将有限者认作非有限者,认作无限者,换句话说,就是将有限者化为无限者,而将无限者化为有限者。
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的存在。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东西、确定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没有有限者,无限者是根本不能设想的。你能不想到一个一定的性质而对性质进行思想和下定义么?因此,最初的东西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而是确定的东西:因为确定的性质不是别的,仅仅是实际的性质;实际的性质是先于思想中的性质的。
哲学的主观来源和进程,也就是它的客观来源和进程。当你思想到性质之前,你先感觉到性质。感受是先于思维的。
无限者是有限者的真实本质——真实的有限者。真正的思辨或哲学不是别的,仅仅是真实的、普遍的经验。
宗教和哲学的无限者,无论现在和过去都不是别的,仅仅是某种有限的东西,某种确定的东西,但是被神秘化了,就是说,一种有限的东西,一种确定的东西,一加以设定,就不是有限的东西,不是确定的东西了。思辨哲学与神学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将实在性或有限性的规定,仅仅通过规定性的否定——就是在这种规定性中,这些规定才成为这些规定——化为无限者的规定和宾词。
诚实与公正对于一切事物都是有益的,对于哲学也是如此。但是哲学要做到诚实和公正的地步,只有承认它的思辨的无限性的有限性,例如承认上帝的本性的秘密仅仅是人的本性的秘密,承认它为了借以产生意识的光明而加在上帝身上的那种黑暗不是别的,仅仅是它自己对于物质的实在性和不可避免性的那种暧昧的、本能的感情。
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从这样的道路,永远不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永远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抽象概念现实化,正因为如此,也永远不能认识精神的真正自由:因为只有对于客观实际的本质和事物的直观,才能使人不受一切成见的束缚。从理想到实在的过渡,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有它的地位。
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事物和本质是怎样的,就必须怎样来思想来认识它们。这是哲学的最高规律、最高任务。
把存在的东西说成它所是的那样,是真实地宜说了真实的东西,看起来却好像是肤浅的;把存在的东西说成它所不是的那样,是不真实地、歪曲地宜说了真实的东西,看起来却好像是深刻的。
真确性、简单性、确定性是真实的哲学的形式标志。
作为哲学的开端的存在,是不能与意识分离的,意识也不能与存在分离。正如感觉的实在是性质,反过来感觉又是性质的实在那样,存在也是意识的实在,而同样地,反过来意识又是存在的实在——识才是实际的存在。精神与自然的真正统一只是意识。
思辨哲学从绝对那里剥去、排入有限事物和经验事物领域内的一切规定、形式、范畴或者用其他名称所表示的东西,恰好包含着有限事物的真正本质,亦即真正的无限者,包含着哲学真正的、最后的秘密。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体的存在形式。只有在空间和时间内的存在才是存在。对于空间和时间的否定,永远只是否定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并不是否定空间和时间的本质。一种无时间性的意志,一种无时间性的思想,一种无时间性的实体,乃是不存在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根本没有时间,也就没有意欲和思维的时间和热望。
在形而上学中事物本质中否定空间和时间,是有最恶劣的实际后果的。只有随时随地采取时间和空间观点的人,才能在生活上有计划,有实践的见识。空间和时间是实践的第一标准。一个民族,如果由于它的形而上学而排除了时间,将永恒的、亦即抽象的、与时间脱离的存在神圣化,也一定会由于它的政治而排除时间,将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反历史的固定原则神圣化。
思辨哲学将脱离时间的发展当作“绝对”的一种形式、一种属性。这种使发展脱离时间的做法,却是思辨哲学任意妄为的一件真正杰作,它有力地证明了思辨哲学家对于“绝对”的所作所为与神学家对于上帝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一样的:上帝具有人的一切欲望而没有欲望爱而不爱,怒而不怒。没有时间的发展,也就等于不发展的发展。“绝对实体自行发展”这个命题,只有颠倒过来,才是一个真实的、合理的命题。所以应当说:只有一种发展的、在时间中展开的实体,才是一种绝对的、亦即真正的、实际的实体。
空间和时间是实际的无限者的显现形式。
没有限制、没有时间、没有痛苦的地方,也就没有性质、没有力量、没有精神、没有热情、没有爱。只有感到痛苦的实体才是必然的实体。没有需要的存在是多余的存在。什么需要都没有的东西,也就没有存在的需要。存在或不存在,是一样的——对于它自己是一样的,对于其他人也是一样的。没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实体。只有能感到的东西才值得存在。只有具有丰富的惨痛经验的实体才是神圣的实体。没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没有实体的实体。没有痛苦的实体不是别的,仅仅是一种无感觉、无物质的实体。
一种哲学,如果不包含被动的原则,一种哲学,如果对无时间的存在、无期间的生存、无盛觉的性质、无实体的实体、无生命无血肉的生命进行思辨——这样一种哲学,就与一切关于绝对的哲学一样,是一种绝对片面的哲学,必然要与经验相对立。斯宾诺莎虽然将物质当作实体的一种属性,却没有将物质当作感受痛苦的原则,这正是因为物所并不感受痛苦、因为物质是单一的、不可分的、无限的,因为物质和与它相对立的思维属性具有相同的特质,简言之,因为物质是一种抽象的物质,是一种无物质的物质,正如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人和自然的本质,但是却没有本质、没有自然、没有人一样。
哲学家必须用人中间那种不研究哲学的、甚至于反对哲学的东西来对抗抽象的思维。必须将被黑格尔贬为注释的东西吸收到哲学的正文里面来。只有这样,哲学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无敌手的、不可推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哲学不应当从自身开始,而应当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我们中间这个与思辨有别的非哲学的、绝对反经院哲学的本质,乃是感觉主义原则。
哲学的主要工具和器官是头脑——这是活动、自由、形而上学无限性、唯心论的来源。同时是心情——这是痛苦、有限性、需要、感觉主义的来源。用理论名词来说,哲学的工具和器官就是思维和直观,因为思维是头脑所需要的,直观感觉是心情所需要的。思维是学派和体系的原则,直观是生活的原则。在直观中我为对象所决定,在思维中我决定对象。思维中我是我,在直观中我是非我。只有从思维的否定中,从对象的确定中,从欲望中,从一切快乐和烦恼的来源中,才能创造出真实的、客观的思想,真实的、客观的哲学。直观提供出于存在直接同一的实体,思维提供出于存在异化了和分离了的间接地本质。因此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与思维结合、被动语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论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
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家就是怎样的,反过来,哲学家的性质,哲学的主观条件和成分,也是它的客观条件和成分。真正的、与生活、与人同一的哲学家,必须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混合血统。纯洁的德国人请不要害怕这种混血!“哲学家文汇”(Acta Philosophorum)已经于纪元1716年表明了这种思想。“如果我们将德国人和法国人比较一下,那么。法国人的心灵比较活泼德国人则比较严正。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气质对于哲学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换句话说:一个父亲是法国人而母亲是德国人的孩子,一定(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具有很好的哲学才能。”完全正确:我们只要将法国人当作母亲,将德国人当作父亲。心情,是女性的原则,是对于有限事物的官能,是唯物论的所在地——这是法国式的想法:头脑,是男性的原则,是唯心论的所在地——这是德国式的想法。心情是革命的,头脑是改良的;头脑使事物成立,心情使事物运动。但是只有运动、激动、欲望、热血、感觉存在的地方,才存在着精神。只有莱布尼兹的智慧,只有他的热情的唯物同时又唯心的哲学原则,才第一次将德国人从他们的哲学上的学究气和经院习气中拯救出来。
在哲学中,一直是将心情当作神学的胸墙。但是,心情恰好是绝对反神学的原则,恰好是人们的神学意义之下的无信仰、无神论的原则。因为心情并不相信别的东西,只相信自己,只相信它的本质的无可辩驳的神圣的绝对实在性。但是不了解心情的头脑,却因为它的任务是分离和区别主体和客体,而心情原来的本质转变为一种与心情不同的,客观的外在本质。当然,对于心情来说,是需要一种别的本质的,然而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与它自己相同的与心情无区别的、与心情不矛盾的本质神学否认心情的真理性、宗教感情的真理性。例如,宗教感情、心情说:“上帝受难”,神学则说:上帝不受难,这就是说,心情否认上帝与人的差别,神学则承认这种差别。
有神论是建立在头脑与心情的分裂上的,泛神论则是在分裂中扬弃这种分裂——因为泛神论将神圣实体仅仅当作内在的超越实体。人本学有神论则无任何分裂。人本学有神论是理智化了的心情,它在头脑中仅仅以理智的方式说出心情以它自己的方式说出的话。宗教仅仅是感情、感觉、心情和爱,就是说,宗教只是对上帝的否定,将上帝溶解在人之中。因此,新哲学既是对神学的否定,而神学是否认宗教感情的真理性的,所以新哲学乃是对宗教的肯定。人本学有神论是自觉的宗教——了解自己的宗教。相反地,神学则在表明上好像优待宗教,实际上否定了宗教。
谢林与黑格尔是对立的。黑格尔代表独立性、自我活动的男性原则,简言之,他代表唯心的原则。谢林则代表承受性和感受性的女性原则:他首先接受费希特,然后接受柏拉图与斯宾诺莎,最后接受波墨,简言之,他代表唯物论的原则。黑格尔缺少直观,谢林缺少思想力和决断力。谢林只是一般的思想家:如果他一与事物接触,一与特殊的、确定的事物接触,他就陷入想象的梦游里去了。谢林的理性主义只是表面的,他的反理性主义才是真实的。黑格尔归结到一种抽象的与反理性原则矛盾的存在和实在,谢林归结到一种与理性原则矛盾的、神秘的、想象的存在和实在。黑格尔用粗野的感性言词补充实在论的缺点,谢林则以美丽的言词补充实在论的缺点。黑格尔以平凡的方式说出不平凡的东西,谢林则以不平凡的方式说出平凡的东西。黑格尔将事物当作单纯的思想,谢林则将单纯的思想——例如上帝的自存性——当作事物。黑格尔为思维的头脑所迷惑,谢林为不思维的头脑所迷惑。黑格尔将非理性化为理性,谢林则相反地将理性化为非理性。谢林哲学是梦境中的实在哲学,黑格尔哲学是概念中的实在哲学。谢林否定幻想中的抽象思维,黑格尔则否定抽象思维中的抽象思维。
黑格尔哲学作为否定性思维的自我否定,作为旧哲学的完成,乃是新哲学的否定性的开始。谢林哲学是带着想象和幻觉的旧哲学,是新的实在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的扬弃,这个矛盾特别是康德就已经提出来了,他看得很清楚!只不过这种矛盾的扬弃是在矛盾的范围以内——是在一种要素的范围以内——是在思维的范围以内。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就是存在,思维就是主体,存在是宾词。逻辑学是思维要素以内的思维,或者是自己思维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或者是无宾词的主体,或者是同时兼为主体的宾词。但是思维要素内的思维还是抽象的:因此它要实在化、外化自己。这个实在化、外化的思想就是自然,一般来说就是实在、存在。但是这个实在之内的真正实在是什么呢?是思维,思维为了将它的无宾词性当作它的真正本质建立起来,于是立即将实在性这个宾词又从自身中排除出去。但是黑格尔并没有因此达到作为存存的存在,达到自由的、独立的、自我满足的存在。黑格尔将客体仅仅想成自己思想自己的思维宾词。存在的宗教和思想中的宗教之间的公认矛盾,在黑格尔哲学中是这样产生的:就是思维无论在什么时候被当作主体,客体和宗教则被看成思想的一个单纯的宾词。
谁不扬弃黑格尔哲学,谁就不扬弃神学。黑格尔关于自然、实在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在逻辑学的结束的地方,甚至使绝对理念作出莫名其妙的“绝对”,以便亲手证明它的来源出于神学的天堂
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正如旧教神学为了与新教作斗争,曾经事实上成为亚里士多德派一样,现在新教神学为了与“无神论”作斗争,依理也必须成为黑格尔派。
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简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存在是存在的,因为非存在是非存在,也就是说,是虎无的,无意义的。
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时间上的发生只推广到自然的外形上,不能推广到自然的本质上。
只有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统一分裂的时候,只有首先通过抽象从存在中取出它的灵魂和本质,然后又在这个从存在中抽出来的本质中找到这个本身空洞的存在的意义和根据的时候,才能从思维中引伸出存在:正如只有将世界的本质与世界任意地分开的时候,才能从上帝引伸出世界。
谁要是按照特殊的实在哲学原则进行思辨,那就是同那些所谓实证哲学家一样:
像一个动物在干枯的草原上
被一个恶魔迷惑着转圈子,
在它的周围却有美丽的、碧绿的牧场。
这个美丽的碧绿的牧场就是自然和人,因为这两种东西就是属于一体的。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
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人是与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没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所以自然是人的根据。
新的唯一实证的哲学,是一切学院哲学的否定。尽管新哲学包含着学院哲学的真理,却否定了这种哲学,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的、特殊的、经院派的性质。新哲学没有暗号,没有特殊的语言,没有特殊的名称,没有特殊的原则:它是思维的人自己。这个人是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自觉的自然本质,是历中的本质,是国家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这个人是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一切对立和矛盾、一切主动的和被动的东西、精神的和感性的东西,政治的和社会的东西的实际上的(并非象中的)绝对同一。这个人知道,被思辨哲学家或者神学家从人分离开来客观化成为一种抽象本质的泛神论本质,不是别的东西,仅仅是人自己的不确定的、但是可以无限地加以规定的本质。
新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否定,也是神秘主义的否定,是泛神论的否定,也是人格主义的否定,是无神论的否定,也是有神论的否定。它是把这一切对立的真理统一为一个绝对独立的、纯粹的真理。
新哲学已经既从消极方面、又从积极方面宣布了自己是宗教哲学。只有将一种实证哲学分析出来的结论当作前提才能在这些结论中认识这种哲学的原则。但是新哲学并不求宠与众人。它是确信自己的,不屑于炫耀自己。但是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主要兴趣在于将现象当作本质、幻觉当作实在、名称当作事物的时代,它必定被看成与它相反的东西。对立的东西就是这样互相补充!在把虚无当作实有、谎言当作真理的地方,当然一定将实有当作虚无、真理当作谎言。在一个地方,人们——可笑的是正当哲学处在对自己怀着决定性的、普遍的失望的时刻——进行前所未闻的尝试,要想将一种哲学完全建立在报章读者的喜爱和意见上面,当然也一定想用在“奥格斯堡通报”中当众污蔑的办法,对学作品进行公正的、基督教的驳斥。德国社会舆论是多么公正,多么道德啊!
一种新的原则,经常是带着一个新的名称出现的,就是说,它将一个名称从低级的、从属的地位中提升到君王的地位,将它当成最高的称号。如果将新哲学的名称、“人”这个名称翻译成自我意识,那就是以旧哲学的意义解释新哲学,将它又推回到旧的观点上去。因为旧哲学的自我意识是与人分离的,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人才是自我意识。
从语言上说,“人”这个名称诚然是一个特殊的名称,然而从实际上说,却是一切名称的名称,“多名”这个宾词当然是属于人的。人经常所称呼的、所说出的东西,也经常说出了他自己的本质。因此语言是人类文化程度高低的标准。“上帝”这个名称,只不过是被人看成最高力量、最高实体、亦即最高感情、最高思想的东西的名称。
“人”这个名称的意义,一般只是指带有他的需要感觉心思的人,只是指作为个人的人,异于他的精神,一般地说,异于他的一般社会性质——例如异于艺术家、思想家、著作家、法官,似乎人所特具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他是思想家、艺术家、法官等等,似乎艺术界、科学界等等各界中的人是在他之外的。思辨哲学在理论上确定了这种人的主要特性与人的分离,从而将完全抽象的性质神圣化为独立的实体。例如黑格尔的“自然权利”第190节便说:“个人在法律上是对象,从道德观点说是主体,在家庭中是家庭成员,在一般公民社会中是公民(作为市民),在这里,从需要的观点说,却是表象(?)的具体名词,人们称之为人,因此,在这里,而且真正说来也只有在这里,说的才是这个意义之下的人。"在这个意义之下,当说到公民、主体、家庭成员、个人时,实际上只是说到同一的实体——人,只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下、从另一种性质来说的。
一切关于法律、关于意志、关于自由、关于没有人的、在人以外甚至在人之上的人格的思辨,都是一种没有统一性、没有必然性、没有实体、没有根据、没有实在性的思辨。人是自由的存在,人格的存在,法律的存在。只有人才是费希特的“自我”的根据和基础。才是莱布尼兹的“单子”的根据和基础,才是“绝对”的根据和基础。
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一种学说在没有找到它的自然基础之前,只能是一种假设。这一点特别对于自由的学说有意义。只有新哲学才能将直到如今仍然是一种反自然主义的、超自然主义的假设的自由自然主义化。
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自然科学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这种建立在相互需要和内在必然性上面的结合,是持久的、幸福的、多子多孙的,不能与以前那种哲学与神学的错配同日而语。
人是国家的一和一切。国家是人的实在化了的、经过发挥的、明确化了的总体。在国家里面,人的主要性质和活动现实化成为特殊的等级,但是这些性质和活动在国家领袖的个人身上重新回到同一性。国家领袖无差别地代表一切等级,在他的面前,一切等级都是同样必要、同样有权利的。国家领袖是普遍的人的代表。
基督教将人这个名称与上帝这个名称用神人这个名称结合起来,从而将人这个名称提高到最高实体的一种属性的地位。新哲学根据真理,将这个属性当作实体,将宾词当作主体——新哲学是实在化了的理念,是基督教的真理。但是,正因为它包含基督教的本质,所以它放弃了基督教这个名称。基督教只是在与真理矛盾中说出了真理。无矛盾的、纯粹的、豪不产假的真理是一种新的真理,是一种新的、自主的人类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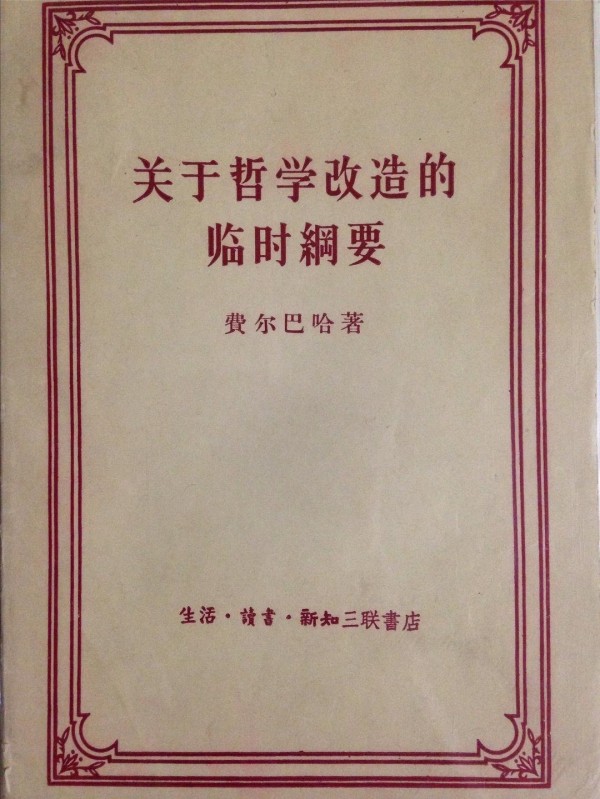
斯宾诺莎是近代思辨哲学的真正创始者,谢林是它的复活者,黑格尔是它的完成者。
“泛神论”是神学(或有神论)——彻底的神学的必然结论。“无神论”是“泛神论”、彻底的“泛神论”的必然结论。
基督教是多神教与一神教的矛盾。
泛神论是带着多神教的宾词的一神教,就是说:泛神论将多神教的那些独立的实体当作一个独立的实体的宾词和属性。例如斯宾诺莎便将作为思维的总体的思维,以及作为广袤物的总体的物质,当作实体亦即上帝的属性。上帝是一个思维的事物,上帝是一个广袤的事物。同一哲学与斯宾诺莎哲学的不同点,仅仅在于它将实体的死的、呆板的东西用唯心论的精神鼓动起来。特别是黑格尔将自我活动、自我判别力、自我意识当作实体的属性。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矛盾的命题:“关于上帝的意识就是上帝的自我意识”,与斯宾诺莎所提出的那个矛盾的命题:“广袤或物质是实体的一种属性”,是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面。这样的命题并无其他意义,仅仅是说:自我意识是实体或上帝的一种属性,上帝就是自我。有神论者归之上帝的那种与实际意识不同的意识,仅仅是一种没有实在性的观念。但是斯宾诺莎说:物质是实体的属性。这个命题的意义无非是说:物质是具有实体性的神圣实体。同一地,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命题的意义也无非是说:意识是神圣实体。
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经应用过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
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
泛神论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对于神学的否定。
正如按照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定义二和命题十),实体的属性或宾词乃实体自身,按照黑格尔,绝对的宾词、主体的宾词一般说来是主体自身。在黑格尔看来,绝对是存在、实体、概念(精神、自我意识)。但是,仅仅被思想成存在的绝对,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是存在。绝对如果被放在这种或那种规定、范畴里面思想,就完全融化为这种范畴、这种规定。因而除此以外,绝对仅仅是一个名称。但是尽管如此,作为主体的绝对仍然是基础,仍然有着真实的主体,有着那种东西,由于这种东西,绝对才不是一个单纯的名称,而是某种东西:这种规定仍然经常具有一种单纯宾词的意义,正如斯宾诺莎的属性那样。
思辨哲学的绝对或无限,从心理学观点来看,只不过是不加规定的、不确定的东西——抽去一切规定的抽象,被看成一种与这种抽象不同而同时又与这种抽象等同起来的实体:从历史观点看来,则只不过是陈旧的、神学——形而上学的、并非有限的、并非人性的、并非物质的、并非确定的、并非创造出来的实体或虚构——,被看成行动的先于世界的虚无。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理性化和现代化了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神学的神圣实体是一切实在性、亦即一切规定性、一切有限性的理想总体或抽象总体,逻辑学也是如此。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可以在神学的天国里再现,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也可以在神圣的逻辑学的天国里再现:例如质,量,度量,本质,化学作用,机械精造,有机体。在神学中,我们对于一切事物都是作二次考察,一次是抽象的,另一次是具体的。在黑格尔哲学中,对一切事物也是作二次考察:先作为逻辑学的对象,然后又作为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对象。
神学的本质是超越的、被排除于人之外的人本质。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超越的思维,是被看成在人以外的人的思维。
正如神学先将人分割为二加以抛弃,以便后来再将这抛弃了的本质与自己等同起来,黑格尔也是先将自然与人的简单的、与自己等同的本质化为多数,加以分割,以便后来把那粗暴地分开的本质在粗暴地调和起来。
形而上学或逻辑学只有在不脱离所谓主观精神的时候,才是一种真实的、内在的科学。形而上学是秘传的心理学。只从性质本身考察性质,只从感觉本身考察感觉,将它们分裂成为两种特殊科学,好像性质是脱离感觉的东西,感觉是脱离性质的东西,这是多么任意,多么粗暴。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与自己分离了的所谓有限精神,正如神学的无限本质不是别的,只是抽象的有限本质一样。
按照黑格尔,绝对精神是显现或实现在艺术、宗教、哲学中。用直率的话来说:艺术、宗教、哲学的精神就是绝对精神。但是不能把艺术和宗教与人的感觉、幻想和直观分离开来,不能把哲学与思维分离开来,简言之,不能把绝对精神与主观精神或人的本质分离开来,而不重返旧的神学观点,而不将绝对精神当作另一种与人的本质有别的精神,亦即当作一种在我们以外存在着的幽灵而使自己迷惑。
“绝对精神”是在黑格尔哲学中还作为幽灵出现的神学的“死亡了的精神”。
神学是对于幽灵的信仰。不过普通神学有它的感性想象中的幽灵,思辨神学有它的非感性抽象中的幽灵。
抽象就是假定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本质。黑格尔哲学使人与自己异化,从而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的整个体系。它诚然将它分离开的东西重新等同起来,但用的只是一种本身又可分离的间接方式。黑格尔哲学缺少直接的统一性,直接的确定性,直接的真理。
从人抽出来而被抛弃了的人的本质与人的直接、鲜明、毫不暖昧的等同,是不能用正面的方式从黑格尔哲学中引出来的,只有作为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才能从其中引申出来。我们只有将这种等同理解成思辨哲学的全盘否定,然后才能理解、才能了解它是不是思辨哲学的真理。虽然一切事物都包藏在黑格尔哲学之中,但是这些事物经常都带着它的否定,它的对立物。
艺术一目了然地证明:绝对精神就是所谓有限的主观精神,因为绝对精神与这种主观精神是不能而且也不该分开的。产生艺术的,是那种以此岸生活为真实生活、以有限者为无限者的感情,是那种以一定的实际本质为最高的神圣本质的热情。基督教的一神教并不包含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原则。只有多神教,只有所谓偶像崇拜,才是艺术和科学的源泉。希腊人只是无条件地、毫不犹豫地将人的形象当作最高的形象,当作神的形象,因而才能达到使他们的造形艺术完美。基督教徒只有实际上否定了基督教神学,将女性的本质当作神圣的本质加以崇拜时,才走向诗歌,当基督教徒对宗教的本质进行想象时,当宗教的本质成为他们的意识对象时,他们就与他们的宗教的本质发生了矛盾,成为艺术家和诗人。彼得拉克由于宗教才悔恨他神圣化他的劳拉的那首诗,何以基督徒不能像异教徒那样具有与他们的宗教观念相适应的艺术作品呢?何以他们没有完全满意的基督形象呢?因为基督徒的宗教艺术由于他们的意识与真理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二失败了。基督教的本质实际上是人的本质,而在基督徒的意识中却是一种另外的非人性的本质。基督应该是人,同时又不是人:他是一种暧昧的东西。但是,艺术只能表达真实的东西,不暧昧的东西。
人性的东西就是神圣的东西,有限的东西就是无限的东西;这个果断的、变成有血有肉的意识,乃是一种新的诗歌和艺术的源泉,这种新的诗歌和艺术在雄壮方面、深刻方面、热情方面都要超过以前的一切诗歌和艺术。对于彼岸事物的信仰,是一种绝对没有诗意的信仰。痛苦是诗歌的源泉。只有将一件有限事物的损失看成一种无限的损失的人,才具有抒情的热情的力量。只有回忆不复存在的事物时的惨痛激动,才是人类的第一个艺术家和第一个理想家。但对于彼岸事物的信仰,却将各种痛苦变成幻像,变成虚构。
从无限的东西引申出有限的东西、从不确定的东西引申出确定的东西的哲学,是永远不能达到对有限的东西和确定的东西作出一个真正的肯定的。从无限的东西中引申出有限的东西,意思就是说:把无限的和不确定的东西确定了,否定了。必须承认没有规定、亦即没有有限性的无限者,只不过是无限者的实在性,因而假定了有限者。但是虚构绝对的否定性仍然是基础,因此被假定的有限性经常又被扬弃了。有限者是无限者的否定,同时无限者又是有限者的否定。关于绝对的哲学乃是一种矛盾。
正如在神学中,人是上帝的真理、实在性——因为一切将作为上帝的上帝现实化、将上帝化为实际本质的宾词,如力量、智慧、善、爱、甚至无限性和人格,都是以异于有限的东西为条件,所以首先要假定在人之中,与人在一起——,同样的,在思辨哲学中,无限的真理也是有限者。
有限事物的真理性,绝对哲学是用间接地、颠倒的方式来宣布的,如果只有当无限者受到规定,亦即不把它假定为无限者,而把它假定为有限者的时候,无限者才存在,才有真理性和实在性,而那么,实际上有限者就是无限者。
真正的哲学的任务,不是将无限者认作有限者,而是将有限者认作非有限者,认作无限者,换句话说,就是将有限者化为无限者,而将无限者化为有限者。
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的存在。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东西、确定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没有有限者,无限者是根本不能设想的。你能不想到一个一定的性质而对性质进行思想和下定义么?因此,最初的东西不是不确定的东西,而是确定的东西:因为确定的性质不是别的,仅仅是实际的性质;实际的性质是先于思想中的性质的。
哲学的主观来源和进程,也就是它的客观来源和进程。当你思想到性质之前,你先感觉到性质。感受是先于思维的。
无限者是有限者的真实本质——真实的有限者。真正的思辨或哲学不是别的,仅仅是真实的、普遍的经验。
宗教和哲学的无限者,无论现在和过去都不是别的,仅仅是某种有限的东西,某种确定的东西,但是被神秘化了,就是说,一种有限的东西,一种确定的东西,一加以设定,就不是有限的东西,不是确定的东西了。思辨哲学与神学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将实在性或有限性的规定,仅仅通过规定性的否定——就是在这种规定性中,这些规定才成为这些规定——化为无限者的规定和宾词。
诚实与公正对于一切事物都是有益的,对于哲学也是如此。但是哲学要做到诚实和公正的地步,只有承认它的思辨的无限性的有限性,例如承认上帝的本性的秘密仅仅是人的本性的秘密,承认它为了借以产生意识的光明而加在上帝身上的那种黑暗不是别的,仅仅是它自己对于物质的实在性和不可避免性的那种暧昧的、本能的感情。
思辨哲学一向从抽象到具体、从理想到实在的进程,是一种颠倒的进程。从这样的道路,永远不能达到真实的、客观的实在,永远只能做到将自己的抽象概念现实化,正因为如此,也永远不能认识精神的真正自由:因为只有对于客观实际的本质和事物的直观,才能使人不受一切成见的束缚。从理想到实在的过渡,只有在实践哲学中才有它的地位。
哲学是关于存在物的知识。事物和本质是怎样的,就必须怎样来思想来认识它们。这是哲学的最高规律、最高任务。
把存在的东西说成它所是的那样,是真实地宜说了真实的东西,看起来却好像是肤浅的;把存在的东西说成它所不是的那样,是不真实地、歪曲地宜说了真实的东西,看起来却好像是深刻的。
真确性、简单性、确定性是真实的哲学的形式标志。
作为哲学的开端的存在,是不能与意识分离的,意识也不能与存在分离。正如感觉的实在是性质,反过来感觉又是性质的实在那样,存在也是意识的实在,而同样地,反过来意识又是存在的实在——识才是实际的存在。精神与自然的真正统一只是意识。
思辨哲学从绝对那里剥去、排入有限事物和经验事物领域内的一切规定、形式、范畴或者用其他名称所表示的东西,恰好包含着有限事物的真正本质,亦即真正的无限者,包含着哲学真正的、最后的秘密。
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体的存在形式。只有在空间和时间内的存在才是存在。对于空间和时间的否定,永远只是否定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并不是否定空间和时间的本质。一种无时间性的意志,一种无时间性的思想,一种无时间性的实体,乃是不存在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根本没有时间,也就没有意欲和思维的时间和热望。
在形而上学中事物本质中否定空间和时间,是有最恶劣的实际后果的。只有随时随地采取时间和空间观点的人,才能在生活上有计划,有实践的见识。空间和时间是实践的第一标准。一个民族,如果由于它的形而上学而排除了时间,将永恒的、亦即抽象的、与时间脱离的存在神圣化,也一定会由于它的政治而排除时间,将既不合法又不合理的、反历史的固定原则神圣化。
思辨哲学将脱离时间的发展当作“绝对”的一种形式、一种属性。这种使发展脱离时间的做法,却是思辨哲学任意妄为的一件真正杰作,它有力地证明了思辨哲学家对于“绝对”的所作所为与神学家对于上帝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一样的:上帝具有人的一切欲望而没有欲望爱而不爱,怒而不怒。没有时间的发展,也就等于不发展的发展。“绝对实体自行发展”这个命题,只有颠倒过来,才是一个真实的、合理的命题。所以应当说:只有一种发展的、在时间中展开的实体,才是一种绝对的、亦即真正的、实际的实体。
空间和时间是实际的无限者的显现形式。
没有限制、没有时间、没有痛苦的地方,也就没有性质、没有力量、没有精神、没有热情、没有爱。只有感到痛苦的实体才是必然的实体。没有需要的存在是多余的存在。什么需要都没有的东西,也就没有存在的需要。存在或不存在,是一样的——对于它自己是一样的,对于其他人也是一样的。没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实体。只有能感到的东西才值得存在。只有具有丰富的惨痛经验的实体才是神圣的实体。没有痛苦的实体是一种没有实体的实体。没有痛苦的实体不是别的,仅仅是一种无感觉、无物质的实体。
一种哲学,如果不包含被动的原则,一种哲学,如果对无时间的存在、无期间的生存、无盛觉的性质、无实体的实体、无生命无血肉的生命进行思辨——这样一种哲学,就与一切关于绝对的哲学一样,是一种绝对片面的哲学,必然要与经验相对立。斯宾诺莎虽然将物质当作实体的一种属性,却没有将物质当作感受痛苦的原则,这正是因为物所并不感受痛苦、因为物质是单一的、不可分的、无限的,因为物质和与它相对立的思维属性具有相同的特质,简言之,因为物质是一种抽象的物质,是一种无物质的物质,正如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人和自然的本质,但是却没有本质、没有自然、没有人一样。
哲学家必须用人中间那种不研究哲学的、甚至于反对哲学的东西来对抗抽象的思维。必须将被黑格尔贬为注释的东西吸收到哲学的正文里面来。只有这样,哲学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无敌手的、不可推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因此哲学不应当从自身开始,而应当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我们中间这个与思辨有别的非哲学的、绝对反经院哲学的本质,乃是感觉主义原则。
哲学的主要工具和器官是头脑——这是活动、自由、形而上学无限性、唯心论的来源。同时是心情——这是痛苦、有限性、需要、感觉主义的来源。用理论名词来说,哲学的工具和器官就是思维和直观,因为思维是头脑所需要的,直观感觉是心情所需要的。思维是学派和体系的原则,直观是生活的原则。在直观中我为对象所决定,在思维中我决定对象。思维中我是我,在直观中我是非我。只有从思维的否定中,从对象的确定中,从欲望中,从一切快乐和烦恼的来源中,才能创造出真实的、客观的思想,真实的、客观的哲学。直观提供出于存在直接同一的实体,思维提供出于存在异化了和分离了的间接地本质。因此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与思维结合、被动语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论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与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
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家就是怎样的,反过来,哲学家的性质,哲学的主观条件和成分,也是它的客观条件和成分。真正的、与生活、与人同一的哲学家,必须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混合血统。纯洁的德国人请不要害怕这种混血!“哲学家文汇”(Acta Philosophorum)已经于纪元1716年表明了这种思想。“如果我们将德国人和法国人比较一下,那么。法国人的心灵比较活泼德国人则比较严正。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气质对于哲学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换句话说:一个父亲是法国人而母亲是德国人的孩子,一定(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具有很好的哲学才能。”完全正确:我们只要将法国人当作母亲,将德国人当作父亲。心情,是女性的原则,是对于有限事物的官能,是唯物论的所在地——这是法国式的想法:头脑,是男性的原则,是唯心论的所在地——这是德国式的想法。心情是革命的,头脑是改良的;头脑使事物成立,心情使事物运动。但是只有运动、激动、欲望、热血、感觉存在的地方,才存在着精神。只有莱布尼兹的智慧,只有他的热情的唯物同时又唯心的哲学原则,才第一次将德国人从他们的哲学上的学究气和经院习气中拯救出来。
在哲学中,一直是将心情当作神学的胸墙。但是,心情恰好是绝对反神学的原则,恰好是人们的神学意义之下的无信仰、无神论的原则。因为心情并不相信别的东西,只相信自己,只相信它的本质的无可辩驳的神圣的绝对实在性。但是不了解心情的头脑,却因为它的任务是分离和区别主体和客体,而心情原来的本质转变为一种与心情不同的,客观的外在本质。当然,对于心情来说,是需要一种别的本质的,然而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与它自己相同的与心情无区别的、与心情不矛盾的本质神学否认心情的真理性、宗教感情的真理性。例如,宗教感情、心情说:“上帝受难”,神学则说:上帝不受难,这就是说,心情否认上帝与人的差别,神学则承认这种差别。
有神论是建立在头脑与心情的分裂上的,泛神论则是在分裂中扬弃这种分裂——因为泛神论将神圣实体仅仅当作内在的超越实体。人本学有神论则无任何分裂。人本学有神论是理智化了的心情,它在头脑中仅仅以理智的方式说出心情以它自己的方式说出的话。宗教仅仅是感情、感觉、心情和爱,就是说,宗教只是对上帝的否定,将上帝溶解在人之中。因此,新哲学既是对神学的否定,而神学是否认宗教感情的真理性的,所以新哲学乃是对宗教的肯定。人本学有神论是自觉的宗教——了解自己的宗教。相反地,神学则在表明上好像优待宗教,实际上否定了宗教。
谢林与黑格尔是对立的。黑格尔代表独立性、自我活动的男性原则,简言之,他代表唯心的原则。谢林则代表承受性和感受性的女性原则:他首先接受费希特,然后接受柏拉图与斯宾诺莎,最后接受波墨,简言之,他代表唯物论的原则。黑格尔缺少直观,谢林缺少思想力和决断力。谢林只是一般的思想家:如果他一与事物接触,一与特殊的、确定的事物接触,他就陷入想象的梦游里去了。谢林的理性主义只是表面的,他的反理性主义才是真实的。黑格尔归结到一种抽象的与反理性原则矛盾的存在和实在,谢林归结到一种与理性原则矛盾的、神秘的、想象的存在和实在。黑格尔用粗野的感性言词补充实在论的缺点,谢林则以美丽的言词补充实在论的缺点。黑格尔以平凡的方式说出不平凡的东西,谢林则以不平凡的方式说出平凡的东西。黑格尔将事物当作单纯的思想,谢林则将单纯的思想——例如上帝的自存性——当作事物。黑格尔为思维的头脑所迷惑,谢林为不思维的头脑所迷惑。黑格尔将非理性化为理性,谢林则相反地将理性化为非理性。谢林哲学是梦境中的实在哲学,黑格尔哲学是概念中的实在哲学。谢林否定幻想中的抽象思维,黑格尔则否定抽象思维中的抽象思维。
黑格尔哲学作为否定性思维的自我否定,作为旧哲学的完成,乃是新哲学的否定性的开始。谢林哲学是带着想象和幻觉的旧哲学,是新的实在哲学。
黑格尔哲学是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的扬弃,这个矛盾特别是康德就已经提出来了,他看得很清楚!只不过这种矛盾的扬弃是在矛盾的范围以内——是在一种要素的范围以内——是在思维的范围以内。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就是存在,思维就是主体,存在是宾词。逻辑学是思维要素以内的思维,或者是自己思维自己的思想--这种思想或者是无宾词的主体,或者是同时兼为主体的宾词。但是思维要素内的思维还是抽象的:因此它要实在化、外化自己。这个实在化、外化的思想就是自然,一般来说就是实在、存在。但是这个实在之内的真正实在是什么呢?是思维,思维为了将它的无宾词性当作它的真正本质建立起来,于是立即将实在性这个宾词又从自身中排除出去。但是黑格尔并没有因此达到作为存存的存在,达到自由的、独立的、自我满足的存在。黑格尔将客体仅仅想成自己思想自己的思维宾词。存在的宗教和思想中的宗教之间的公认矛盾,在黑格尔哲学中是这样产生的:就是思维无论在什么时候被当作主体,客体和宗教则被看成思想的一个单纯的宾词。
谁不扬弃黑格尔哲学,谁就不扬弃神学。黑格尔关于自然、实在为理念所建立的学说,只是用理性的说法来表达自然为上帝所创造、物质实体为非物质的、亦即抽象的实体所创造的神学学说。在逻辑学的结束的地方,甚至使绝对理念作出莫名其妙的“绝对”,以便亲手证明它的来源出于神学的天堂
黑格尔哲学是神学最后的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正如旧教神学为了与新教作斗争,曾经事实上成为亚里士多德派一样,现在新教神学为了与“无神论”作斗争,依理也必须成为黑格尔派。
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存在的根据在它自身中,因为只有存在才是感性、理性、必然性、真理,简言之,存在是一切的一切。存在是存在的,因为非存在是非存在,也就是说,是虎无的,无意义的。
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时间上的发生只推广到自然的外形上,不能推广到自然的本质上。
只有思维与存在的真正统一分裂的时候,只有首先通过抽象从存在中取出它的灵魂和本质,然后又在这个从存在中抽出来的本质中找到这个本身空洞的存在的意义和根据的时候,才能从思维中引伸出存在:正如只有将世界的本质与世界任意地分开的时候,才能从上帝引伸出世界。
谁要是按照特殊的实在哲学原则进行思辨,那就是同那些所谓实证哲学家一样:
像一个动物在干枯的草原上
被一个恶魔迷惑着转圈子,
在它的周围却有美丽的、碧绿的牧场。
这个美丽的碧绿的牧场就是自然和人,因为这两种东西就是属于一体的。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
自然是与存在没有区别的实体,人是与存在有区别的实体。没有区别的实体是有区别的实体的根据——所以自然是人的根据。
新的唯一实证的哲学,是一切学院哲学的否定。尽管新哲学包含着学院哲学的真理,却否定了这种哲学,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的、特殊的、经院派的性质。新哲学没有暗号,没有特殊的语言,没有特殊的名称,没有特殊的原则:它是思维的人自己。这个人是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自觉的自然本质,是历中的本质,是国家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这个人是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一切对立和矛盾、一切主动的和被动的东西、精神的和感性的东西,政治的和社会的东西的实际上的(并非象中的)绝对同一。这个人知道,被思辨哲学家或者神学家从人分离开来客观化成为一种抽象本质的泛神论本质,不是别的东西,仅仅是人自己的不确定的、但是可以无限地加以规定的本质。
新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否定,也是神秘主义的否定,是泛神论的否定,也是人格主义的否定,是无神论的否定,也是有神论的否定。它是把这一切对立的真理统一为一个绝对独立的、纯粹的真理。
新哲学已经既从消极方面、又从积极方面宣布了自己是宗教哲学。只有将一种实证哲学分析出来的结论当作前提才能在这些结论中认识这种哲学的原则。但是新哲学并不求宠与众人。它是确信自己的,不屑于炫耀自己。但是正因为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这个主要兴趣在于将现象当作本质、幻觉当作实在、名称当作事物的时代,它必定被看成与它相反的东西。对立的东西就是这样互相补充!在把虚无当作实有、谎言当作真理的地方,当然一定将实有当作虚无、真理当作谎言。在一个地方,人们——可笑的是正当哲学处在对自己怀着决定性的、普遍的失望的时刻——进行前所未闻的尝试,要想将一种哲学完全建立在报章读者的喜爱和意见上面,当然也一定想用在“奥格斯堡通报”中当众污蔑的办法,对学作品进行公正的、基督教的驳斥。德国社会舆论是多么公正,多么道德啊!
一种新的原则,经常是带着一个新的名称出现的,就是说,它将一个名称从低级的、从属的地位中提升到君王的地位,将它当成最高的称号。如果将新哲学的名称、“人”这个名称翻译成自我意识,那就是以旧哲学的意义解释新哲学,将它又推回到旧的观点上去。因为旧哲学的自我意识是与人分离的,乃是一种无实在性的抽象。人才是自我意识。
从语言上说,“人”这个名称诚然是一个特殊的名称,然而从实际上说,却是一切名称的名称,“多名”这个宾词当然是属于人的。人经常所称呼的、所说出的东西,也经常说出了他自己的本质。因此语言是人类文化程度高低的标准。“上帝”这个名称,只不过是被人看成最高力量、最高实体、亦即最高感情、最高思想的东西的名称。
“人”这个名称的意义,一般只是指带有他的需要感觉心思的人,只是指作为个人的人,异于他的精神,一般地说,异于他的一般社会性质——例如异于艺术家、思想家、著作家、法官,似乎人所特具的基本特征并不在于他是思想家、艺术家、法官等等,似乎艺术界、科学界等等各界中的人是在他之外的。思辨哲学在理论上确定了这种人的主要特性与人的分离,从而将完全抽象的性质神圣化为独立的实体。例如黑格尔的“自然权利”第190节便说:“个人在法律上是对象,从道德观点说是主体,在家庭中是家庭成员,在一般公民社会中是公民(作为市民),在这里,从需要的观点说,却是表象(?)的具体名词,人们称之为人,因此,在这里,而且真正说来也只有在这里,说的才是这个意义之下的人。"在这个意义之下,当说到公民、主体、家庭成员、个人时,实际上只是说到同一的实体——人,只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下、从另一种性质来说的。
一切关于法律、关于意志、关于自由、关于没有人的、在人以外甚至在人之上的人格的思辨,都是一种没有统一性、没有必然性、没有实体、没有根据、没有实在性的思辨。人是自由的存在,人格的存在,法律的存在。只有人才是费希特的“自我”的根据和基础。才是莱布尼兹的“单子”的根据和基础,才是“绝对”的根据和基础。
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一种学说在没有找到它的自然基础之前,只能是一种假设。这一点特别对于自由的学说有意义。只有新哲学才能将直到如今仍然是一种反自然主义的、超自然主义的假设的自由自然主义化。
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自然科学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这种建立在相互需要和内在必然性上面的结合,是持久的、幸福的、多子多孙的,不能与以前那种哲学与神学的错配同日而语。
人是国家的一和一切。国家是人的实在化了的、经过发挥的、明确化了的总体。在国家里面,人的主要性质和活动现实化成为特殊的等级,但是这些性质和活动在国家领袖的个人身上重新回到同一性。国家领袖无差别地代表一切等级,在他的面前,一切等级都是同样必要、同样有权利的。国家领袖是普遍的人的代表。
基督教将人这个名称与上帝这个名称用神人这个名称结合起来,从而将人这个名称提高到最高实体的一种属性的地位。新哲学根据真理,将这个属性当作实体,将宾词当作主体——新哲学是实在化了的理念,是基督教的真理。但是,正因为它包含基督教的本质,所以它放弃了基督教这个名称。基督教只是在与真理矛盾中说出了真理。无矛盾的、纯粹的、豪不产假的真理是一种新的真理,是一种新的、自主的人类的行动。